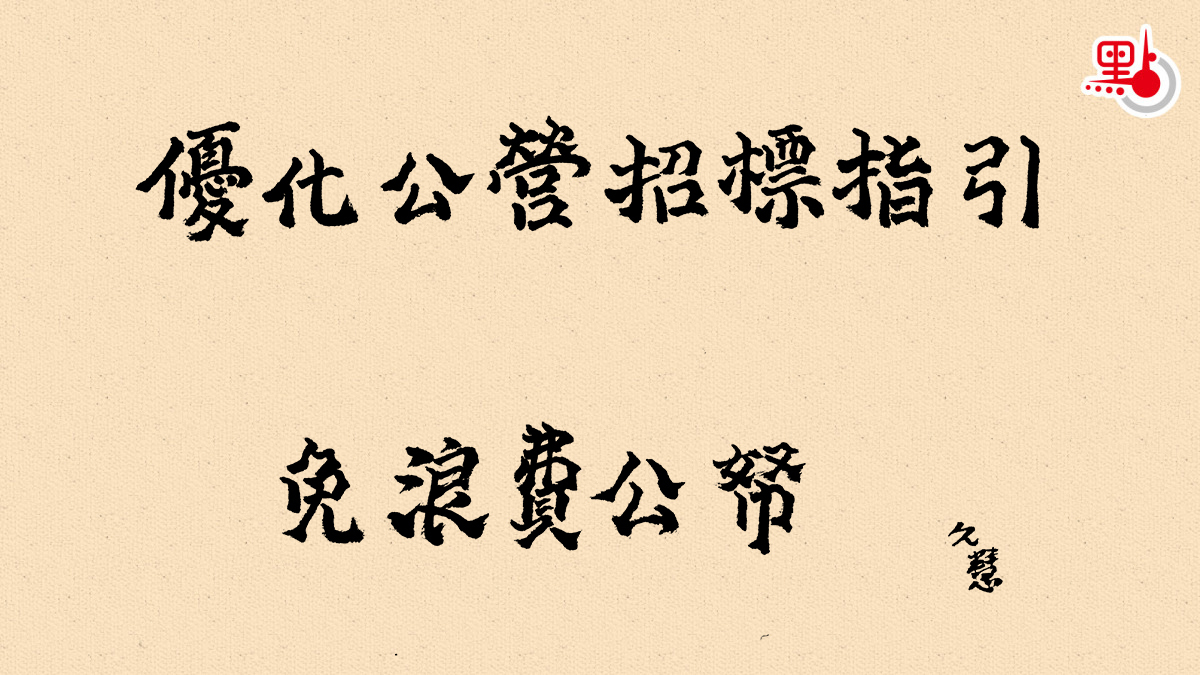
文/鄭久慧
早前筆者在《修訂政府招標指引 避免向潛在投標商披露「預估合約金額」》一文中,探討了由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訂立、規範政府部門採購、僅提供英文版的《政府採購招標程序》(《招標程序》)的未盡妥當之處,包括未明確指明在何種情況下,允許或禁止政府人員披露「預估合約金額」,同時《招標程序》亦未明確規定披露方式,恐衍生選擇性僅向部分投標者而非所有投標人告知「預估合約金額」的情況,影響公平投標,更可能變相令某些公司長期中標、導致項目成本一直居高不下,現時政府財赤,須盡快堵塞規例漏洞,減少公帑浪費。
廉政公署未明文禁止公共機構披露預估合約金額
另一邊廂,在規管公共機構方面,有廉政公署訂立的《公共機構採購防貪指南》(《採購防貪指南》),這個指南備有中英文版。中文版(見鏈接:https://cpas.icac.hk/UPloadImages/InfoFile/cate_43/2023/0ecff105-f3ba-41f9-8898-6de6efbfb428.pdf)第28頁列明:「避免向潛在投標商披露預估合約金額,以免他們在擬備報價單/標書時受到影響,削弱投標商之間的競爭。」
據筆者進行文本分析的統計所得,整份指南中「避免」出現了15次,「禁止」出現了23次,兩詞程度有深淺之分。上述第28頁的句子使用「避免」,而非「禁止」,反映出廉署在訂立時,並未立意嚴格禁止「披露預估合約金額」的行為,某種程度上可視作給予公共機構職員酌情權,可自行斟酌是否披露「預估合約金額」。然而,這個「酌情權」應該怎樣行使呢?細看整份《採購防貪指南》,廉政公署並未明確界定在何種情況下應允許或禁止此類披露,也未明確規定如果披露此類預估合約金額,須向所有意向投標者披露,否則不得向任何單一意向投標者披露。
頗為令人費解的是,在指南第27頁,廉署列明:「確保所有潛在投標商均能獲得足夠並且一致的資料,以便制定最具競爭力的報價單/標書,尤其是對於制定報價單/標書所需的關鍵資料(例如有關規格的充分細節、過去使用量的數據、需要提交的文件)。」可見廉署對其他範疇是寫得很清晰的,為何唯獨對足以影響入標價、對中標與否至關重要的「預估合約金額」,廉署不作類似的明文規範?
財赤下預估合約金額大概率意味着獲諮詢投標者的入標價
細看《招標程序》第17頁與《採購防貪指南》第28頁的解說文字,均在試圖解釋,避免透露「預估合約金額」,是為了防止所有投標者圍繞着該預估價值去報價,從而導致政府及公營機構無法獲得最低投標價。然而根據筆者問詢具廿年投標經驗的外判商,實際上如果投標者真正參與競爭,當局擔憂的這個情況根本不可能發生。
反而,筆者獲知另一個更值得關注的大問題,就是在公共預算面臨嚴重赤字的現狀下,公職人員披露的「預估合約金額」,就近乎等同「披露獲部門諮詢的投標者的意向報價」,對與該部門在意向書(EOI)階段密切溝通的供應商造成不公平。
為什麼這麼說呢?這就要從現行招標機制說起,現時政府的採購形式是根據《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的規定,政府如採購價值超逾136萬港元的貨品或一般服務、超逾300萬港元的顧問服務,以及超逾700萬港元的建造及工程服務,一般須採用公開競投的招標程序,以獲取最符合經濟效益的投標書。低於這個額度的採購,無須經政府物流署,只須由部門內部採購,而通常入標此類非物流署標書的,多為中小企。低於5萬元的小型招標,只需獲得兩至三間不同公司的報價,就符合要求。
一般來說,這些由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的採購部自行決定中標者的投標,不少是配合該部門特定職能而「度身訂造」的專業系統或服務,標書內容頗為學術及專門,部門中的「實際用家」(user)會主動出擊去尋找供應商,經過在市場裏一輪篩選,找到「心儀供應商」並保持密切溝通,確保自己所擬定的標書內容是「技術可行」及「專業用詞恰當」,亦確保出標時其他供應商亦能理解標書內容。
「實際用家」從「心儀供應商」不但能諮詢到大量技術意見,更重要的是獲知該供應商的意向報價(ball-park figure),作為申請預算的用途。如此就衍生出兩個可能性。其一,在過往公共財政充裕時,部門並不會直接將「心儀供應商的意向報價」作為「預估合約金額」,會多申請一些,給自身留一點預算空間,避免未來要「將價就貨」,價低者得,讓出價最低但質素未必好的入標者中標,部門難以採購到最適合的服務或系統。同時,多出來的預算也能用作未來改良優化之用,免得到時又要再申請經費。其二,現時公共財政緊張,部門所申請的「預估合約金額」預算,很大機會等同「心儀供應商的意向報價」,一旦公職人員選擇性披露「預估合約金額」,很大機會意味着獲諮詢投標者(「心儀供應商」)的入標價被洩露,造成投標不公。
至此,有人可能會問,獲部門諮詢的「心儀供應商」這麼誠實嗎?向公職人員報價多少,入標價也須維持一樣嗎?首先,在數以月計的磋商溝通中,為釐清政府或公營機構的「實際用家」的技術需求,「心儀供應商」不僅提供面談會議、系統演示,電郵及電話溝通更是多不勝數。基於對公職人員的信任,獲諮詢的投標者會傾向於使用已經呈交的意向報價,避免用更低的價格入標,因為這會讓公職人員感到尷尬,意味着他們在意向書階段沒有盡全力爭取低價,在財赤下尤其顯得辦事不力。同時,較低入標價可能會造成較低的中標價,拉低部門的實際支出,分分鐘降低部門下一個財政年度能申領到的預算總額,在財赤下部門對這種情況尤其敏感,絕不樂見。有經驗的投標者向筆者分享真實案例,由於在報章看到某部門採取積極措施節省開支,於是決定入標該部門某項目時,將已呈交的意向報價打個九折,自減10%,從而展現對社會的承擔。不久接獲該部門聯絡人來電,質疑是否填錯數值,要求澄清並詢問原因,為何入標價低於已呈交的意向報價。據知,這並非該投標者首次遇到「自行降價入標」而被部門「詢問」的情況。
從以上「默契」或者「制約」中,不難看出「預估合約金額」很大機會等於獲部門緊密諮詢磋商的投標者的已呈交意向報價,亦很大機會等於此投標者的實際入標價。在公共財政緊絀、一塊錢最好掰開兩半花的情況下,一旦公職人員選擇性披露「預估合約金額」,引至其他獲偏愛的投標者以低於「預估合約金額」約10%左右入標,那麼就可以輕鬆擊敗呈交意向價格的投標者,而且兩者之間的差價非常少,不公平之處顯而易見。故此約束政府部門的《招標程序》與約束公營機構的《採購防貪指南》,不應繼續模模糊糊,而應訂明披露準則,才能確保公平競爭,讓有限的公帑用得其所。
完善現有規例 避免「老江湖供應商」採用「試價手段」長年壟斷項目
完善《招標程序》與《採購防貪指南》有以下四方面的必要性。
第一,對於獲部門諮詢的投標者來說,若其屬於正當商家,老老實實呈交意向報價(ball-park figure),部門採用這個價錢為「預估合約金額」。該投標商入標時也跟隨這個意向報價,皆因若報一個更低價,就可能接近虧本。此時假如公職人員應用相關規例容許的酌情空間,選擇性向其他公司披露「預估合約金額」,這位誠實的投標者就很大機會失去這個項目,數以月計的磋商預備付諸流水。
第二,不能否認的是,現有的規例用「通常情況下」(Normally)一詞來給予公職人員酌情空間,允許他們在「例外」情況下披露「預估合約金額」,能增加招標的靈活性。例如所收到的意向報價遠高於部門能申請到的預算總額,但該部門確實需要進行這項採購,因為所涉的產品或服務是必須的。在這種情況下,公職人員向投標者披露「預估合約金額」,讓投標者心中有數,將有助部門在可負擔的預算內採購到所需的產品或服務。對於一些從未參與該部門項目投標的新供應商,披露金額將有助他們「破冰」,從而鼓勵令更多公司入標,加強競爭。然而,在這種情況下,應規範披露的方式(書面/口頭)及要求無差別地向所有供應商披露,杜絕濫用酌情權。
第三,優化規例能促進競爭,避免「老江湖供應商」採用「試價手段」,長年壟斷項目。由於各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的工作性質和流程和大部分私人企業不同,設備及項目需求特殊,採購項目具備專業技術性,故此合資格投標者並不算多。即使定期招標,也可能長期被若干早已演化成「老江湖」的老牌大供應商,利用「試價」的方式投中項目。「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試價手段是筆者最近聽聞的案例。以下為模擬的類似案例,數字只是例子,並非實數。由於組件過時,某部門進行招標購置新系統,先向現有系統的「老江湖供應商」索取意向價,豈料遭「開天殺價」叫價60萬港幣,部門感覺不合理,轉向另一規模較小的新供應商索取報價,新供應商花費數月時間了解部門需求,磋商最新改良方案,務求度身訂造最適合「實際用家」的系統。基於誠信,新供應商根據成本加上少量利潤,向政府人員呈交意向報價約30萬,大大低於「老江湖供應商」的60萬,部門感覺合理,亦由於財政緊張,於是就以30萬為「預估合約金額」,進而申請預算經費,順利獲批,於是展開正式招標程序。入標時,新供應商也誠實地以30萬為入標價,豈料結果揭盅,卻是「老江湖供應商」以僅僅低於新供應商幾個百分點的價格,贏得這項投標。很難不令人聯想到是否有人利用「披露預估合約金額」的模糊規例,選擇性以非書面方式透露了等同新供應商入標價的「預估合約金額」,讓「老江湖供應商」勝出。
第四,鼓勵更多新企業參與投標,遏止壟斷,確保公平競爭,是社會進步的原動力。以上案例中,「老江湖供應商」在提供特定系統的領域有多年歷史,人脈廣且產品尚算可靠,由於市場上能夠提供該產品的供應商屈指可數,因此常受邀參與政府及公營部門的意向書階段。奈何其策略是先「開天殺價」,報出非常高的意向價,企圖「測試」部門可接受的最高價。
如此一來,採用「試價手段」就能試出兩個結果:要麼,下一步部門或公共機構真的與「老江湖供應商」進入招標前的磋商階段,要求其提交意向報價及具體技術方案。此舉變相證明部門或公共機構早已坐擁足夠預算資金(60萬),那麼接下來「老江湖供應商」即使選擇高價入標,中標率亦頗高,但受害的將是納稅人辛辛苦苦賺的公帑;要麼,部門或公營機構不再繼續與報天價的「老江湖供應商」進行下一步的具體磋商,而是邀請其他有誠意的供應商提交意向報價及進行項目商談。但由於此類特定系統的供應商數量非常有限,部門依照規例必須獲得一定數量的入標書,否則可能流標。故此,「老江湖供應商」最終仍會收到招標邀請,同時可能通過他們的「廣泛人脈」,獲知部門已經物色其他供應商尋求新合作契機。於是乎,「老江湖供應商」就進入「落地還錢」階段,例如聯絡他們合作過的相熟公職人員,希望獲得「預估合約金額」的提示。誠然,公職人員可能會出於善意行事,希望更多潛在供應商提交投標,以便促進競爭,亦可能因為規例寫得模模糊糊,酌情權大,並不明文禁止披露「預估合約金額」,那麼何不提示一下相識及合作多年的「老江湖供應商」,讓他們知悉最新市價,讓他們的入標價「落地」。未來雙方若能再度合作,公職人員就省卻與新供應商磨合的精力和時間,無須熟習新系統的操作。對「老江湖供應商」來說,報個「海鮮價」並非難事,「開天殺價」與「落地還錢」之間的報價彈性雖然大,但很大可能該部門現有的系統就是他們提供的,更新到新系統的附加成本非常低,即使「開天殺價」不成,「落地還錢」也絕不虧本,甚至盈利仍非常可觀。
不當披露「預估合約金額」侵害公平正當的營商環境
在上述雙方「皆大歡喜」的背後,變相助長了壟斷,受害的不僅是廣大納稅人,亦是投入巨大人力物力時間陪着公職人員磋商數月,一切從零開始,協助部門的「實際用家」釐清各類需求,然後基於對公職人員的信任及堅守自己營商誠信而如實報價,將意向報價(即「預估合約金額」)當成入標價,最終因小額差價而輸了投標的新供應商。故此,完善《招標程序》與《採購防貪指南》刻不容緩!
不當披露「預估合約金額」侵害公平正當的營商環境,弊端可歸納為以下七點。
其一,這些產品成熟且「人脈廣泛」的「老江湖供應商」可以不斷「試價」,以頻繁測試來爭取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可能接受的最高價格。
其二,即使數個政府部門及公營機構均需要採購此類專門產品,但由於這些部門與機構之間根本不會交流招標經驗,互通情報,共建資料庫去記錄供應商的誠信歷史,從而篩查黑名單,故此不良供應商頻繁的投標不當行為或舞弊行為就不會被曝光。
其三,劣幣驅逐良幣,如上述實例所顯示,不良供應商能透過獲得「預估合約金額」,淘汰那些新進入行業、專注於技術研發而非「人際關係」的誠信供應商。
其四,在規模較小的供應商者被淘汰後,部門及公營機構幾乎缺乏其他選擇,供應商名單越來越短,那些仍留在市場的規模較大的「老江湖供應商」就可大幅提高價格,缺乏競爭造成採購價格居高不下,浪費公帑。
其五,在這種營商趨勢下,企業會傾向於投入更多資金於市場推廣、建立人際關係及增進交誼聯絡,而用於核心技術研發、高難度突破和注重細節技術工作的資金將不斷減少,最終受害的是整個社會。
其六,即使公職人員並非向部分投標者,而是向所有潛在投標者都披露了「預估合約金額」,以保持招標的「公平競爭」,並讓提交意向報價的投標者知道他們必須提供更低的價格才能成交,但這個做法亦不應任意經常使用,因為這相當於披露了獲諮詢意向報價的投標者的入標價,某些基於誠信報價、質量較高的供應商,利潤不高,根本難以承受更低的價格。
其七,其他入標者並未參與試探可接受的最高價,但卻承受着來自一些試探過部門和公營機構的「老江湖供應商」的巨大出價壓力。這些「老江湖」熟悉現有系統,故此更有資本令報價「海鮮化」,掀起減價戰。若缺乏妥善監管公職人員披露「預估合約金額」的法例,由於不少投標列明絕非「價低者得」,部門內部的權衡亦會左右何人中標,故此仍存在貪污或舞弊的風險,例如「老江湖」往往擁有更多資源來提供「甜頭」,也坐擁更強的人脈網絡,最終分分鐘誘使公職人員「偏袒」高價入標的「老江湖」。
優化政府的《招標程序》與廉政公署《採購防貪指南》的五項建議
有鑒於上述的考量,筆者建議作出以下五項優化。
其一,明確界定在哪些情況下允許公職人員披露「預估合約金額」,以及哪些情況下嚴禁披露。
其二,披露「預估合約金額」應盡量做到公平合理,例如公職人員應向所有投標者公開披露,且此類披露只能以書面形式進行,且必須在投標截止日期前至少7個工作日進行。
其三,一旦在招標過程中披露「預估合約金額」,政府部門或公營機構必須在投標結束後將投標結果(中標價格和中標者)告知每一位投標者。
其四,當局應組織部門內部檢討會議,讓參與招標意向書階段及實際投標遴選的實際用家、技術人員與採購部人員分享他們在採購事宜、與不同供應商打交道方面的經驗及心得,尤其是加強識別入標者的「試價手段」,避免「老江湖供應商」有機可乘。
其五,鼓勵採購人員和實際用家分享使用特定專業系統或產品的體驗,探索最新技術,從而提升公職人員的採購能力。具廿年投標經驗的供應商告訴筆者,歷年來所收到的標書文件的技術含量並不高,資訊不足以協助投標者了解用家的需求,從而準備具有競爭力的意向報價及提案。若公職人員本身對某些特定的專門系統缺乏理解與認知,就會越發依賴現有的供應商來幫助他們準備招標文件的技術參數(Technical specifications)。但這些現有供應商(「老江湖」)通常不願意披露太多技術信息,因為這會助長他們的競爭對手了解具體用家的需求,協助對手合理評估系統造價,增加對手中標的機會率。於是乎,標書本身提供的資訊很少,新供應商只能在短至兩三周的招標期,不斷聯絡部門,希望釐清實際的技術需求,但由於公職人員可能過度依賴現有供應商,造成自身也不太了了,現有供應商傾向於「拖字訣」,擠牙膏般告知,最終新供應商收到的回覆不但慢,而且資訊量少。招標限期前,仍未能掌握足夠資訊的新供應商,要麼選擇不入標,要麼「破釜沉舟」,抱着虧本的決心咬咬牙「含淚入標」。故此,筆者建議各部門及公營機構,應像政府物流署的那樣,全數上載所有招標文件,供公眾自由下載,容許全民監督招標文件的內容是否完善。此外,應在採購科闢出專職人員,主動聯絡全部潛在投標者,收集意見,查找不足,全面檢討在標書文件或招標流程中發現的流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