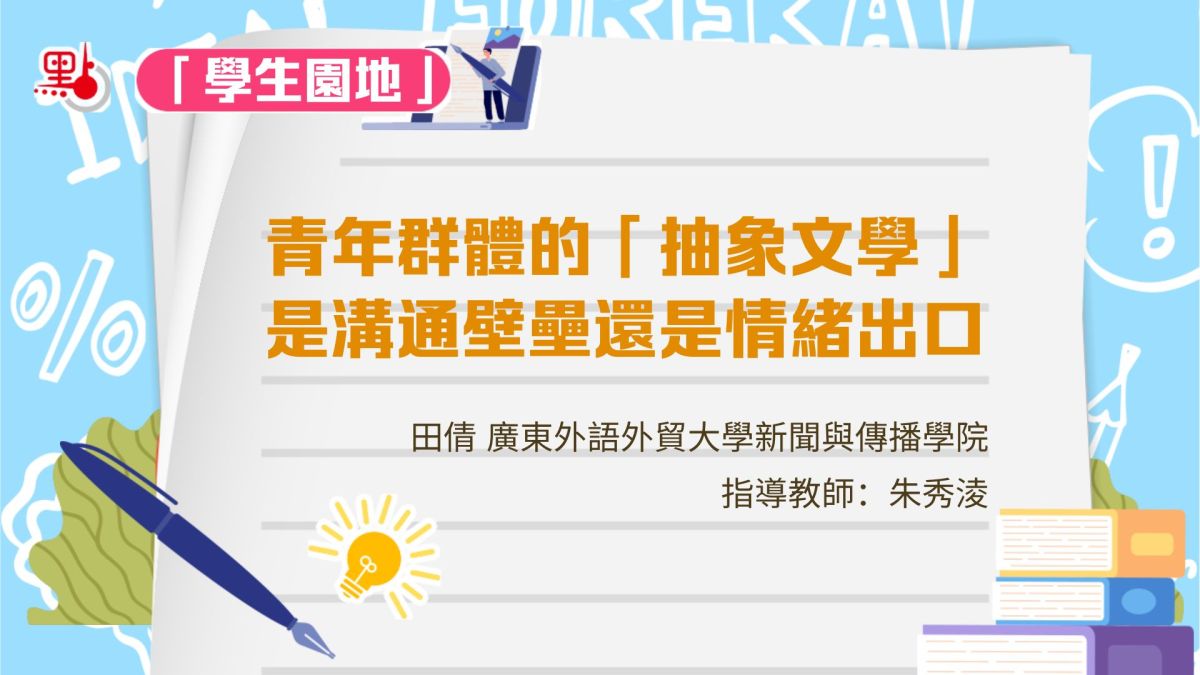
青年群體的「抽象文學」 是溝通壁壘還是情緒出口
田倩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現如今,一打開手機軟件,你肯定會看到這樣的句子:「鼠鼠我呀,今天又被老闆當牛馬使了。」「躺了,但還沒完全躺,畢竟牛馬還得交房租。」等等,這些看似荒誕的「抽象話」,已經成為了年輕人的新型社交貨幣。鼠鼠文學裏,「鼠鼠我啊,這輩子是沒機會出下水道咯」,把生活的困頓化作老鼠的自嘲;躺平文學裏,「躺着挺好的,反正地球離了誰都會轉」,滿是對內卷的無聲抵抗;牛馬文學更加直白,「牛馬罷了,牛馬的命不是命,幹就完了」,充滿了打工人的卑微與無奈。這些荒誕的表達,既不是單純的賣慘,也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當代青年群體的「情緒鎧甲」——用玩笑話來化解尷尬,用自嘲來抵禦真實世界的暴擊。
當代青年人的生活,並不像幻想中的那麽美好,而是被時代洪流卷進了無限壓力中。學業上,千軍萬馬擠過獨木橋,考研、考公、考編的競爭強度持續攀升;職場叢林中,內卷和996如影隨形,「35歲被優化」的陰影提前籠罩;社交場合,人際關係的複雜、人性的醜惡,都在製造精神焦慮,加大精神壓力。處於這樣的「高壓鍋」中,直白傾訴「我好難」都會成為罪過,會陷入玻璃心、矯情的評價陷阱中,而抽象文學正好提供了這樣一種隱晦、荒誕的情緒舒緩的新出口。
把自己代入「鼠鼠」,將人生困境形象地轉化為下水道的掙扎;以「牛馬」自居,把職場卑微弱小稀釋為自嘲的調侃,這種看似晦澀、荒誕的表達,本質上是給當代年輕人的高壓、抑制的情緒打開安全閥,用戲謔來解構現實的沉重,讓尖銳的疼痛,在玩梗中轉化為可以共享、可以共鳴的情緒碎片。在當下的社交網絡中,「鼠鼠文學」「小鎮做題家」「牛馬」的共鳴鏈不斷延長,千萬年輕人在玩梗中得到「原來不是我一個人這樣」的確認,得到心理上的寬慰,孤獨感也在慢慢消散,個體苦難匯進群體共情的洪流中。
其實,抽象文學在年輕群體風靡,背後還隱藏着年輕人對代際溝通差異的防禦性表達。當他們向長輩袒露工作的艱辛,學習的困苦,收到的常常是「現在的年輕人一點兒苦都吃不了,想當年……」的否定,通常會讓他們更加封閉,感覺不被理解,更有甚者還會陷入自我懷疑。而發布一條牛馬擺爛日記,「我上班的怨氣可以復活十個邪劍仙了」,懂的同齡人看到會秒懂,立馬共情,不懂的長輩則自動「失語」,這種圈層加密的表達,像給情緒築起防護牆,既能釋放壓力,又能夠巧妙躲開代際沖突的火力。同時,抽象文學還成為促進青年群體構建圈層認同的社交暗號,這些獨特的表達,如同隱形門檻,將有共同經歷、興趣的年輕人圈定,形成我們懂彼此之間的親密共同體。
抽象文學雖是年輕人的解壓閥,但是當其邊界失控,便會異化為溝通的絆腳石。在日常交流中,若年輕人不分場合的使用抽象梗替代清晰表達,就會導致理解不暢,交流障礙,讓有效信息的傳遞陷入泥沼。當抽象從情緒出口,成為交流壁壘,語言連接世界的功能被消解,這種個性表達就會走向自我封閉的反面。此外,更需要警惕的是,過度抽象可能會催生自嗨式共情,當擺爛、躺平被抽象文學反覆包裝成潮流,消極情緒在共鳴中不斷被放大,原本就是階段性陷入困難的年輕人,在「鼠鼠永無天日」的文案轟炸中,可能陷入政治無用、努力無用的精神泥潭,從而讓抽象文學異化為吞噬青春活力、成為懶惰懦弱的藉口。
年輕人需要情緒出口,社會各界也應該理解抽象文學背後的壓力和孤獨,但表達的本質是連接、溝通,而不是隔絕。我們應該適度使用抽象,要保持自己的理性,用抽象來疏解壓力,凝聚同頻者,不能讓它結成困住自己的繭房。當我們用「鼠鼠文學」自嘲後,仍有直面生活的勇氣,藉助「牛馬」調侃後,依然懷有積極向上的力量,才能真正成長為自洽合格的大人。
相關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