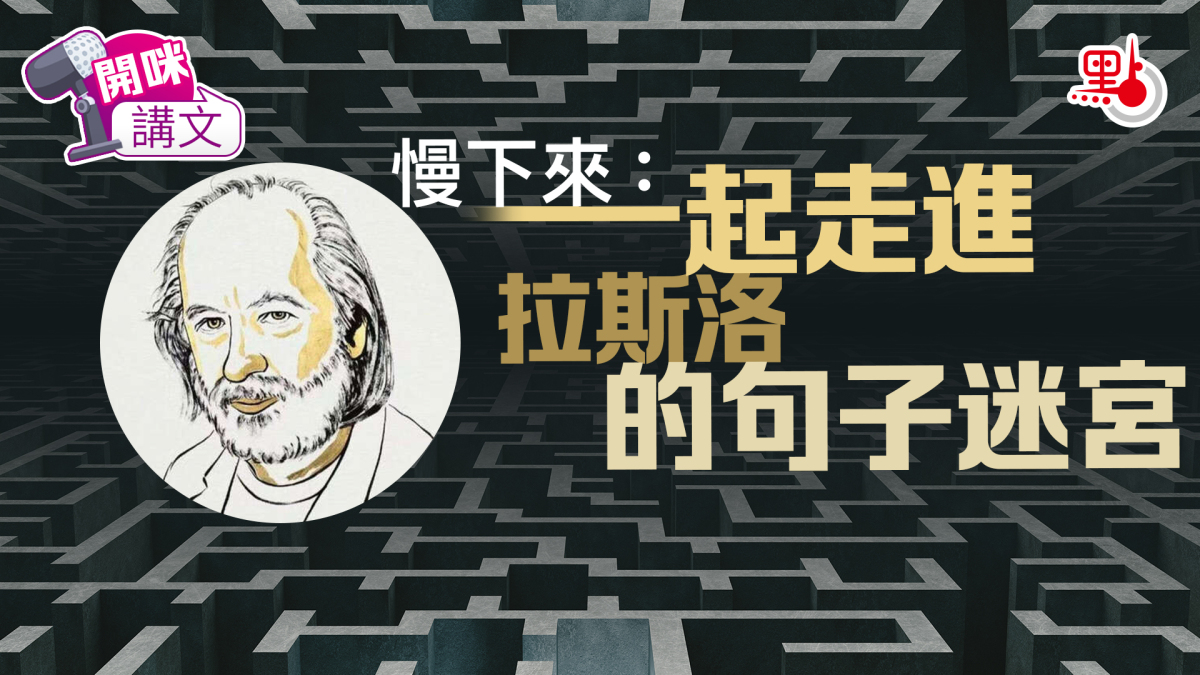
文/徐曦
諾貝爾文學獎是當今世界影響力最大的文學獎項,每年都會引發坊間眾多猜測,甚至國外一些博彩公司會給潛在的獲獎者列出不同的賠率榜單,吸引大眾下注。在世界文壇享有盛名的阿特伍德、拉什迪、托馬斯·品欽、安·卡森和科爾姆·托賓等作家是榜上的常客。日本小說家春上村樹常年出現在榜單上,雖然人氣很旺,卻一直未能折桂。喜歡跑馬拉松的他,在諾獎的賽上似乎還要一直「陪跑」下去。過去幾年,中國小說家殘雪獲獎呼聲很高,但去年的諾獎頒給了韓國女作家韓江,短期內亞洲女作家獲獎的機率估計不高。
10月9日,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如期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揭曉。此次的諾貝爾文學獎頒授給了71歲的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László Krasznahorkai),以表彰「他那引人入勝且富有遠見的作品,在末世般的恐怖之中,重申了藝術的力量」( 「for his compelling and visionary oeuvre that, in the midst of apocalyptic terror, reaffirms the power of art」)。拉斯洛是誰?他寫過些什麼作品?這或許是許多讀者跟我一樣的疑問。相比英法西德等歐洲大國的文學,匈牙利文學在中國的譯介並不多,也更少進入普通讀者的視野。雖然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的詩句:「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在中國廣為人知,但若說要列出幾位當代匈牙利作家的名字,恐怕多數人都難以做到。喜好東歐文學的讀者可能讀過馬洛伊·山多爾(Márai Sándor)、阿戈塔·克里斯托夫(Agota Kristof)、伊姆雷·凱爾泰斯(Imre Kertész,2002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但「克拉斯諾霍爾卡伊·拉斯洛」這個拗口的名字即使對不少外國文學研究者來說也顯得陌生,以至於我在朋友圈看到有學者以半開玩笑的口吻說:「每年就靠諾貝爾文學獎榜單來補文學常識了。」
1954年1月5日,拉斯洛出生在距離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200多公里的久洛(Gyula),這個邊境小城毗鄰羅馬尼亞,以中世紀的古堡遺址和地熱溫泉聞名。他的父親是位律師,母親是位公務員。拉斯洛最初追隨父親的志向,在匈牙利的最高學府厄特沃什·羅蘭大學修讀法律,但他真正的興趣卻在文藝,後來就轉到了文學院。1983年,他以研究馬洛伊·山多爾的論文獲得匈牙利語言和文學的學位。1985年,他的首部小說《撒旦探戈》一經出版即獲好評,令他在匈牙利文壇嶄露頭角。隨後他不斷推出新作,並陸續被譯介為德文和英文,逐漸受到國際文壇的矚目。2013年,《撒旦探戈》獲得美國的最佳翻譯圖書獎(Best Translated Book Award);2014年,《西王母下凡》(Seiobo There Below)再次獲得同一獎項;2015年,他成為首位獲得國際布克獎(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的匈牙利作家。他的作品得到不少名家的青睞,蘇珊·桑塔格就曾稱讚他對末世感的精準描繪堪與果戈里和梅爾維爾媲美。
雖然拉斯洛迄今出版過9部長篇小說,5部中篇小說,2部短篇集,還有諸多零散的短篇、散文和訪談,但中文譯介並不多,目前正式出版的僅有4部,因此拉斯洛對多數中國讀者來說依然陌生。他首部被譯為中文的是成名作《撒旦探戈》,出版於2017年,距離原作初版已有32年之久。另外3本分別是《仁慈的關係》(短篇集,2020),《反抗的憂鬱》(2023)和《世界在前進》(短篇集,2025)。
實際上,拉斯洛在中國愛好歐洲文藝片的影迷群體中或許更有名,因為他的小說被以大量長鏡頭知名的匈牙利傑導演貝拉·塔爾(Béla Tarr)改編成了電影,包括長達7個多小時的同名巨作《撒旦探戈》(1994)和《鯨魚馬戲團》(2000)已是影史經典。他還參與過多部塔爾電影的編劇工作,其中《都靈之馬》(2011)獲得了第61屆柏林國際電影節的銀熊獎。或許是因為少年時代玩過爵士樂,拉斯洛成名後喜歡與藝術家跨界合作。他曾與德國畫家馬克思·諾依曼(Max Neumann)合作出版圖文並茂的《動物在其中》(Animal Inside)和《追尋荷馬》(Chasing Homer),後者的每章開頭還有一個二維碼,掃碼即可聆聽由匈牙利音樂家米克洛什·西爾維斯特(Miklos Szilveszter)專門為此書創作的樂曲。這種多媒體的設置令讀者在獲得多重感官享受的同時,亦可激發我們對於文本(虛構)與世界(現實)複雜糾纏的思考。
如何閱讀拉斯洛
在歐美文壇,拉斯洛被視為一位後現代小說家,他的小說艱澀難懂,因為他喜歡使用迷宮般的長句。有時甚至一個句子長達數頁,綿延不斷,環環相套,初讀的人會有一種喘不過氣來的窒息感和不知道該在何處停頓的茫然。例如《反抗的憂鬱》的開頭:
無論在鐵道邊值班的鐵道工怎樣顛三倒四地猜測解釋,無論火車站站長多少次越來越確信無疑地衝到站台上翹首張望,這列由蒂薩河畔出發駛向喀爾巴阡山腳下,並將凍成了冰坨的匈牙利南部大平原連接在一起的客運列車始終沒有到來(「唉,這是怎麼搞的,難道這趟列車蒸發掉了……?」鐵道工帶着一臉的嘲諷、無可奈何地揮揮手說)。由於這列總共只有兩輛、只會在所謂「特殊情況」下才投入運行的由質量很差的硬座車廂和一個老掉牙了的、毛病繁多的424型蒸汽車頭拚組而成的救援列車比原本對它就缺少約束力的列車時刻表上所規定的出發時間遲發了一個半小時,因而讓當地人不得不揣着盡可能保持的冷靜與惴惴不安的期盼接受這列由西邊駛來的客車晚點的現實,耐心等待它行駛完最後的五十公里路程,最終能抵達目的地。(余澤民譯)
可以試着開口朗讀一下,是否有些吃力?或許是考慮到讀者吃不消,中譯本將開頭處理成了兩個句子。對照英譯本,我們會發現這兩個句子其實是一個長句:
SINCE THE PASSENGER TRAIN CONNECTING THE icebound estates of the southern lowlands, which extend from the banks of the Tisza almost as far as the foot of the Carpathians, had, despite the garbled explanations of a haplessly stumbling guard and the promises of the stationmaster rushing nervously on and off the platform, failed to arrive (「Well, squire, it seems to have disappeared into thin air again …」 the guard shrugged, pulling a sour face), the only two serviceable old wooden-seated coaches maintained for just such an 「emergency」 were coupled to an obsolete and unreliable 424, used only as a last resort, and put to work, albeit a good hour and a half late, according to a timetable to which they were not bound and which was only an approximation anyway, so that the locals who were waiting in vain for the eastbound service, and had accepted its delay with what appeared to be a combination of indifference and helpless resignation, might eventually arrive at their destination some fifty kilometres further along the branch line. (George Szirtes 譯)
然而,據說匈牙利語的原文句子更長,就是母語者讀起來也同樣覺得費勁!那麼,作為外國讀者,我們又當如何來進入拉斯洛的文本世界呢?翻譯過他多部作品的余澤民的這段話可以作為我們探索拉斯洛用長句所營造的敘事迷宮的指南針:「讀拉斯洛的書,無論是《撒旦探戈》,還是《仁慈的關係》,你都必須調整好呼吸,絕不能一目十行。因為節奏是閱讀、理解他作品的關鍵,你必須適應,並跟隨作家講述的沉穩速度,就像盯着銀幕上緩慢移動的長鏡頭。延綿不斷的陰濕,悶聲不響的殘忍,讓人頭皮發麻的絕望貫穿全書,一個個克拉斯諾霍爾卡伊式的複雜長句接力,纏絞,確如火山爆發時殷紅的熔岩順着地勢緩慢地流淌,流過哪裏,哪裏就是死亡。」
在如今這個信息爆炸,飛速向前的社會,我們整日忙碌不停,不要說去品讀小說詩歌,連休閒看劇都要開兩倍速。拉斯洛的長句,則迫使我們慢下來,進入小說的迷宮,去細細體味當下和思考歷史。如果我們將閱讀比喻作旅行,那麼拉斯洛並非是一位巧舌如簧、催促遊客走馬觀花的導遊,而更像是一位邊走邊聊,陪伴我們在匈牙利山水中跋涉的朋友。走馬觀花的旅行固然便捷快速,可所得所思甚少;跋山涉水的旅程艱難費勁,但留下來的體驗和回憶卻更多。
拉斯洛的中國情結
雖然此前中國讀者對拉斯洛所知不多,但他卻可以稱得上是最了解中國的當代匈牙利作家。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拉斯洛常年旅居歐美和亞洲各地,並多次到過中國。1991年,拉斯洛以記者的身份首次遊歷中國,就受到中國文化的深深震撼。此後,他陸續收藏了不少有關中國的書籍,尤其喜歡讀《道德經》和李白的詩,也仰慕傳統儒家文化。他甚至有一個中文名「好丘」,既可解釋為「美好的山丘」,也可理解為「喜好孔子」。1998年,他再次來到中國,在朋友余澤民(拉斯洛作品最重要的中譯者,知名匈牙利當代文學翻譯家)的陪伴下,遊覽了曲阜、洛陽、西安和成都等地,尋訪李白當年的足跡。
他把九十年代數次在中國旅遊的經驗和對東方文化的觀察寫進了三本書中:《烏蘭巴托的囚徒》(The Prisoner of Urga,1992),《北山,南湖,西路,東河》(A Mountain to the North, a Lake to the South, Paths to the West, a River to the East, 2003)和《天空下的廢墟與憂愁》(Destruction and Sorrow Beneath the Heavens, 2004)。不過目前這些作品都還沒有完整的中譯本,對拉斯洛心目中的中國和東方文化,我們只能從譯者余澤民的幾篇序言和回憶中窺得一二。東方文化,尤其是道家思想是否對拉斯洛的創作觀念產生過影響?東方形象和故事在他的虛構世界中佔有何種位置?他的遊記如何呈現了傳統文化在當代社會的延續與變化?這些都是值得探究的跨文化論題。
諾獎對外國文學的譯介和閱讀有着巨大的推力。據澎湃新聞報道,在諾貝爾文學獎公布的3小時內,拉斯洛作品僅在當當網上的銷量就突破了萬冊。我們希望出版界能借諾獎的東風,推出更多精準的譯本,讓讀者能夠盡可能全面領略拉斯洛文字的魅力。同時也期待學界更深入的研究,幫助我們更清晰地認知拉斯洛在世界文學版圖上的位置及其創作與東方文化的隱秘關聯。
更多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