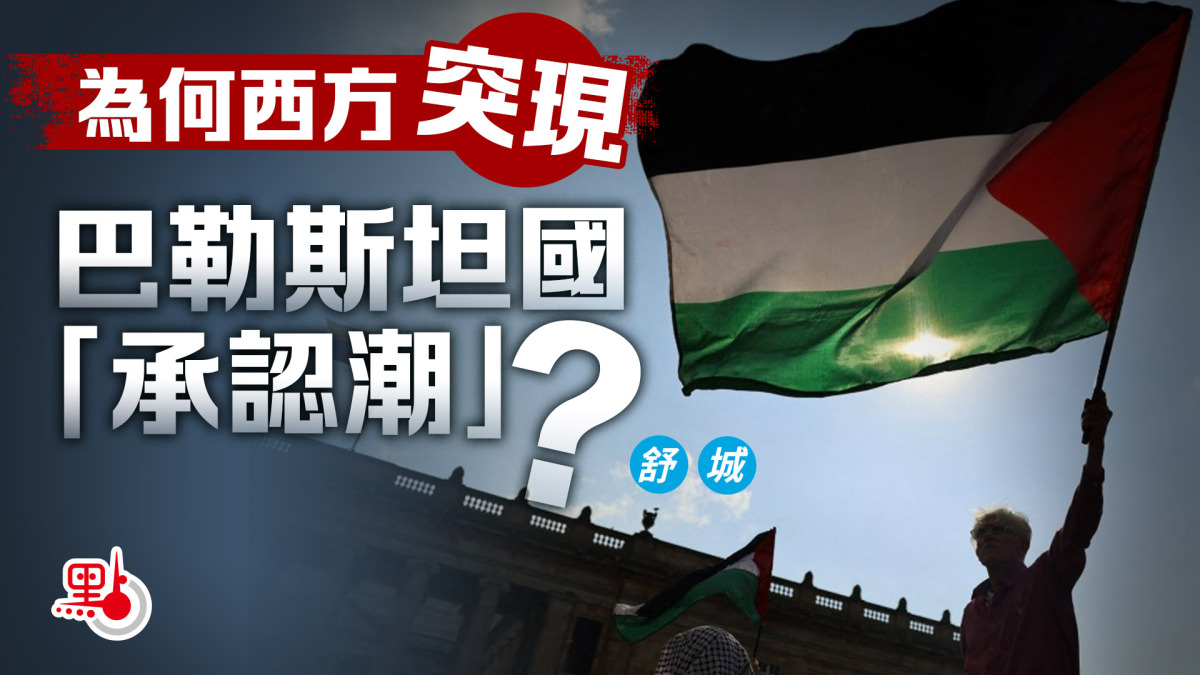
文/舒城
7月31日,加拿大總理卡尼宣布將在9月聯合國大會上承認巴勒斯坦國,為這場由法國點燃、英國跟進的西方外交「承認潮」再添薪火。各國立場雖存差異——法國無預設條件,英國以以色列改善加沙狀況為要挾,加拿大則要求巴勒斯坦2026年排除哈馬斯參與大選並實現「非軍事化」——卻共同折射出一個殘酷現實:加沙的人道災難已衝破西方傳統親以立場的堤壩。當210萬巴勒斯坦人被饑荒吞噬時,繼續沉默等同於共謀。
這場承認潮絕非偶然,而是多重危機疊加的必然。以色列的持續空襲導致加沙經濟需70年才能恢復戰前水平,15.5萬名孕婦和哺乳期女性在空襲中掙扎求生,糧食援助被劫持的指控與「絕望平民搶奪物資」的現實形成觸目驚心的對比;以色列在約旦河西岸加速擴建定居點,試圖在地理上肢解未來巴勒斯坦國領土,西方承認行動是對此的「法理防禦」;特朗普政府一邊向以色列提供百億美元軍援,一邊將承認巴勒斯坦國斥為「獎勵哈馬斯」,甚至威脅加拿大「貿易協議難了」,暴露其調解者面具下的霸權邏輯。
然而,承認巴勒斯坦國只是起點,其象徵意義大於實質。巴勒斯坦早在2012年成為聯合國觀察國,獲140餘國承認,但建國的核心障礙——領土主權、以色列撤軍、耶路撒冷地位——依然無解。更尖銳的矛盾在於西方附加的「民主枷鎖」:加拿大要求巴勒斯坦「非軍事化」,卻無視以色列對西岸的軍事佔領;法國推動排除哈馬斯,卻迴避加沙民眾在封鎖與轟炸中對抵抗組織的複雜依賴。這種「既要巴勒斯坦建國,又剝奪其自衛權」的邏輯,恰是「兩國方案」屢次流產的病灶。
這場承認潮本質是國際社會對「兩國方案」的搶救性行動——若再不承認,巴勒斯坦或將在地理與法理上被徹底抹除;而和平的微光,仍需穿越強權與仇恨的漫長黑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