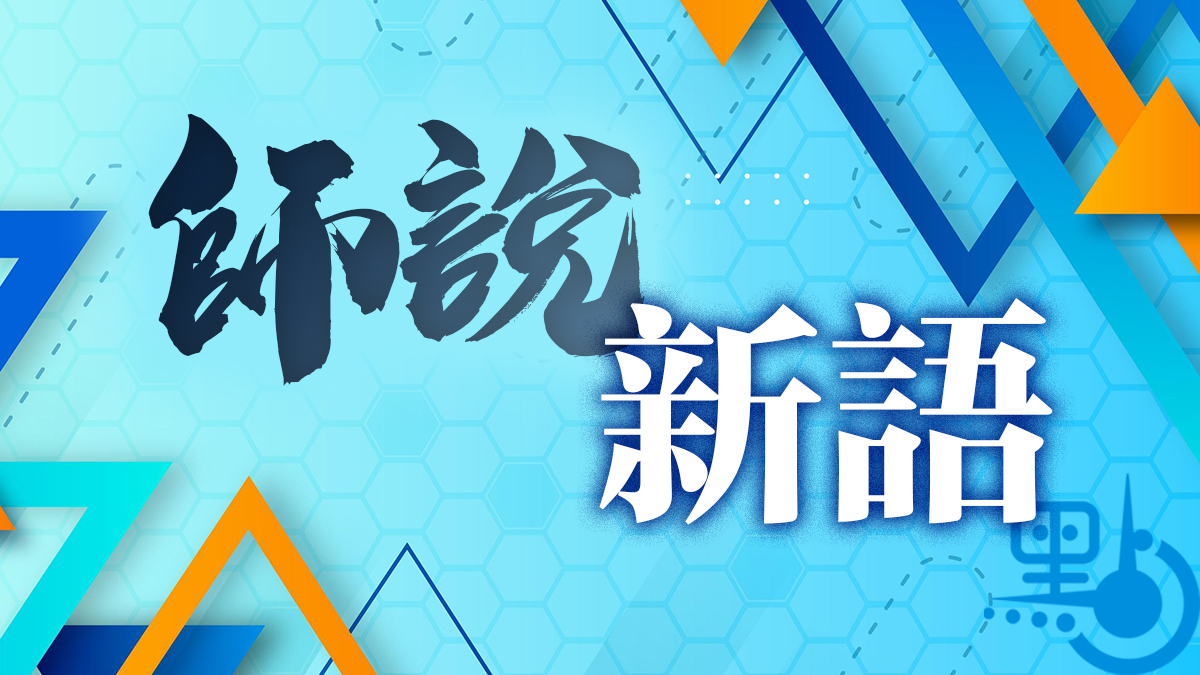
文/張琳
教師,這個塑造着下一代的群體,肩上的責任可謂不輕,但他們的身心健康卻往往被忽視。只有當悲劇發生時,社會才會短暫地將目光投向他們。最近發生西貢小學女教師高處墮下的不幸事件,給我們敲響了警鐘,教師的心理健康值得關注,而這些問題又被我們忽略太久了。說到底,教師的壓力誰來管?壓力過大後,學校或社會是否真的提供了足夠的支援?這些問題,值得我們好好反思。
香港的教師壓力有多大?
其實,這宗悲劇並非孤立事件,香港教師早已處於高壓的工作環境中,面對着巨大的心理壓力。2019年,天水圍一名小學圖書館主任因工作壓力選擇輕生,當時引起了不小的關注,但遺憾的是,這些聲討和關注最終沒有轉化為長遠的制度改進。近年來,隨着香港少子化趨勢的加劇,學校招生壓力越來越大,殺校危機日益逼近,教師們的「鐵飯碗」不再穩固。一些Band 3學校的教師特別感到吃力。有中學教師坦言:「我們既要保證教學質量,又要策劃招生活動,這種雙重壓力正在透支教師熱情。」
此外,很多教師缺乏其他職場經驗,擔心一旦學校關閉,自己將無法適應其他行業。這種對未來的不確定感,與日常的繁重工作一起,讓不少教師感到焦慮不安。更糟糕的是,傳統文化中對分享心理壓力的羞恥感,讓許多教師選擇壓抑情緒,導致心理問題越積越深。根據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2023教師身心健康問卷調查,近9成的教師在過去一周感到疲乏,逾6成感到洩氣,近半教師感到焦急、憤怒和無助,只有3.9%的教師在過去一周沒有負面情緒。據調查結果顯示,教師的壓力來源仍主要來自學校行政工作(84.8%)、教學(59.9%)、新增的政策要求(59.7%)、學生學習差異擴大(56.9%)及學生的情緒問題(51.6%),每項均超過半數教師感到受壓。這些數據背後,是一個個無法喘息的教師群體。
教育界可以做些什麼?
正如事件所警示的,教師的心理健康管理需要更系統、更專業的方式,而不是僅僅依賴臨時的「頭痛醫頭」式處理。要真正幫助教師從壓力中解脫出來,香港教育界需要制定一套全面的支援計劃。首先,學校必須重視教師的心理健康,設立專門的心理支援服務,聘請專業心理輔導員,為教師提供情緒管理和心理干預。教聯會建議撥出資源給辦學團體和學校,為教師提供正向心理學短期課程,提升教師的抗逆力和輔導學生能力,以改善學界師生的負面情緒。其次,應該減輕教師的行政負擔。現在,不少教師的時間被大量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和形式化的評比活動佔據,這些事情耗時耗力,卻與核心教學價值無關。學校和教育局需要重新審視教師的工作內容,取消那些無謂的應酬性任務,並減少頻繁的會議時間,讓教師有更多精力專注於教學和學生的成長。
此外,為了緩解教師對未來的焦慮,教育局應該推出支援計劃,合理安排教師轉校或轉業及公積金暫緩提取方案。這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他們對殺校或失業的恐懼。最重要的是,學校和教育機構需要鼓勵開放的溝通環境。教師之間應該有更多的機會互相支持,建立一個信任和共享的同儕網絡,讓教師不再因分享壓力而感到羞恥。最後,應該考慮引入常規的心理健康評估機制,確保能及早發現問題,並提供有效的干預措施,對教師的心理狀況進行長期跟進。
過去發生的種種不幸,其實都在告訴我們一個簡單卻深刻的道理:教師的心理健康,不僅僅是他們自己的問題,也是影響教育質量的大事。正如心理學家羅傑斯所言:「當人不再害怕正向感情的施與受,才更能夠欣賞別人。」我們需要的不是一兩次的輿論討論,而是一次徹底的行動改變。教師並不是機器,他們需要一個健康、支持性的環境,才能繼續用心教書育人。唯有如此,香港的教育環境才能真正走向可持續發展,也才能避免下一次悲劇的發生。
(作者為未來教育協會學生事務部總監)





